
贾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
纪念 解冻时节
——《解冻时节》代序
by 李辉
------------------------------1---------------------------

1981年左右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与学生们,后排右起:陈思和、赠画颇为、范伯群、李辉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在二十年前,当时他刚刚获准从监督劳动多年的印刷厂,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重操旧业。
中文系在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楼房多年失修,记得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总是格吱格吱发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后来,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在课堂教学之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作品和掌故。
后来,我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喝得最多的是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再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但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两人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当时吟诵出一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是杜甫的诗句,写于安史之乱之后。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已有二十一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不免显得懵懂。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然而,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眼光观望着一切,更多时候,不是靠经验或者知识来与新的环境接触,而是完全靠兴趣、直觉和性格。
当时真正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刻。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一个新时代,仿佛早在那里做好了准备,在我们刚刚进校不久就拉开了帷幕。印象中,当时的复旦便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令人兴奋、新奇的戏剧。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给,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就传来为他平反昭雪的消息;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竞选对手而各自拉起竞选班子;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会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同学发表《伤痕》《杜鹃啼归》,点燃了许多人的文学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变得成熟起来。思想在自由流动,视野在渐渐拓宽,知识在不断丰富。二十年来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在这所可爱校园里开始起步。
引发出我这样一些感触的历史场景,当然就包括着与贾先生最初的接触。不久前我到上海,先生说他正在整理1978年前后的日记。他说我的名字大概在1978年年底时候开始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不过,最初他写成“小李”,而不敢写出我的名字。他说他有所顾虑,害怕会牵连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直接写出我的名字。他告诉我这些往事时,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我很感动。为他的善良,为他对学生的厚爱而感动。
触动我的还有先生的余悸。新旧时代转换,人生大落大起,季节乍暖还寒,不少他那种经历的人自然而然产生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是历史的产物。这样的余悸,也许早已成为远远消失的陈迹,渐渐被人淡忘。但当我一封又一封整理先生1972-78年间写给任敏师母的几十封家书时(这次选载的是一部分),这样的感触,便又成了我了解、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的重要心理准备。同时,一个变得陌生而遥远的时代,也就再度浓墨重彩地在那些字里行间凸现出来。
------------------------------2---------------------------

八十年代李辉与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
先生保留下来的这些信,真实而完整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背影。从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到对个人处境每日变化的描述;从购物细节,到生活叮嘱;从在印刷厂监督劳动,到回到中文系资料室重操旧业……六、七年间个人的琐碎生活,无不映衬着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动人魂魄的历史瞬间。一旦联系到他们的命运变化,联系到产生这些家书的时代环境,它们就显得并非普通平淡。
解冻时节的生动记录。
对于他这种身背“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的人来说,对于许多曾经被冰冻封存起来的人来说,1972年可以说是一个解冻时节的开始。
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先生在将近三十年前写给师母的信。
那次,我到上海,他递给我一摞信,说:“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上面这封信写于1972年5月21日,是这批信中的第一封。
“1972年?我还在念初中哩!”
当时读完这封信,我脱口便是这样一句。的确,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来说,1972年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那一年与前一年其实很难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对贾先生,以及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几代人,它的意味却极为深远。
一切均因不久前的林彪事件而发生潜在的历史变化。
无数文革的参与者,肯定最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变化。林彪事件的发生,不仅仅将领导层的矛盾冲突,以一种激烈、充分戏剧性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更无情动摇了人们业已形成的盲目崇拜、狂热投入的信念。于是,均衡被打破,偶像也不再成为偶像。大张旗鼓的运动方式开始变得如同虚张声势的演出,受到不少人的冷落或者消极应付。可以说,不管是否清醒意识到,对不少有识之士而言,他们内心开始出现忧虑、疑惑与沉思。历史的理性判断,或多或少成为人们的一种愿望和内在要求。
冰冻的情绪、思想,开始萌发新的生机。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心里萌生出希望。
与之相伴随,被疯狂、高压、严酷捆绑得令人几乎喘不过气的生活,也渐渐趋于松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贾先生这样一些被管制的“异类”,所处的环境也就开始有所改善,周围的压力不再那么严重。这一年之后的一些家书能够保留下来,无疑与这一现实变化有关。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和同学们顽皮活泼地度过1972年的时候,在遥远的上海,会有一位长者用特殊心情,写出这样的家书。并且,几年之后,我成了他的学生,他们家里的常客。再过二十年,又成了这些信的读者。
------------------------------3---------------------------

贾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
十多年前,当我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时,我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像胡风夫人梅志、路翎夫人余明英、贾植芳夫人任敏等这样一些受难者的妻子,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多么相似!她们背负着历史的磨难,承受着甚至超过丈夫承受的压力,在风风雨雨中走过。她们未尝一日淡忘过对亲人的思念,她们始终坚守着正义的信念。即便没有机会与亲人重逢,即便亲人也不知道她们的现状,但正是她们的存在,正是她们这种坚韧,成为亲人们精神的支柱,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当时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受难的妻子们”,正是想表达出我的这种敬意。
在认识先生和师母并且逐渐了解到他们的人生故事之后,这对个头一样矮小、一样精瘦的夫妻,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魁梧而高大的形象。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磨难。环境险恶,人心叵测,可是他们从未失去过做人的根本。正直、善良、坦荡、乐观,构成了他们的人格。我知道,不同时期的弟子们谈到对先生的敬意和感激时,常常也就包括师母在内。
在某种程度上,师母经历的磨难更加令人通彻心骨。
当年因为胡风案件爆发,先生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师母也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很快,在1958年底从上海被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师母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揭发师母在一位上海朋友家里的时候曾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又再度被关进了高原监狱。
师母初入狱时,凑巧看守所所长也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当女囚犯头目,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也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到。这便是饥荒岁月。在青海,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位牧民犯人饿得难以忍受,便央求师母帮助弄一碗牛奶喝。她想方设法偷来一碗,没想到,那牛奶是公安局长的,结果她被关禁闭,戴上了手铐。
从此,她被罚从囚室里往外抬每天饿死的犯人尸体。尽管她个头矮小,体弱无力,可是,她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常常是每次抬完回到房间,她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1962年,她出狱了,回到山西襄汾贾植芳的家乡,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先生仍在监狱,她必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后来,果然是她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她的出狱并不是正式释放,而是当时那里实在无粮,让她自寻活路。临行时还留给她一句话:“先让你回去,什么时候要你来你就来。”
回到家乡,师母首先想到的是尽量打听到先生的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先生后来回忆的那个动人细节:“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先生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师母和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了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先生她要来探望他的消息,也许她更愿意让他感到惊奇。
她来到先生的住所。时已中午,先生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
先生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师母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感人的一幕。
我的叙述没有一点儿加工,甚至比师母的回忆还要简略、平淡。可是,当年在他们住的那个小阁楼房间里第一次听到她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沉默了好久。很多年后再写到这些,我仍然感到一股激动撞击心胸。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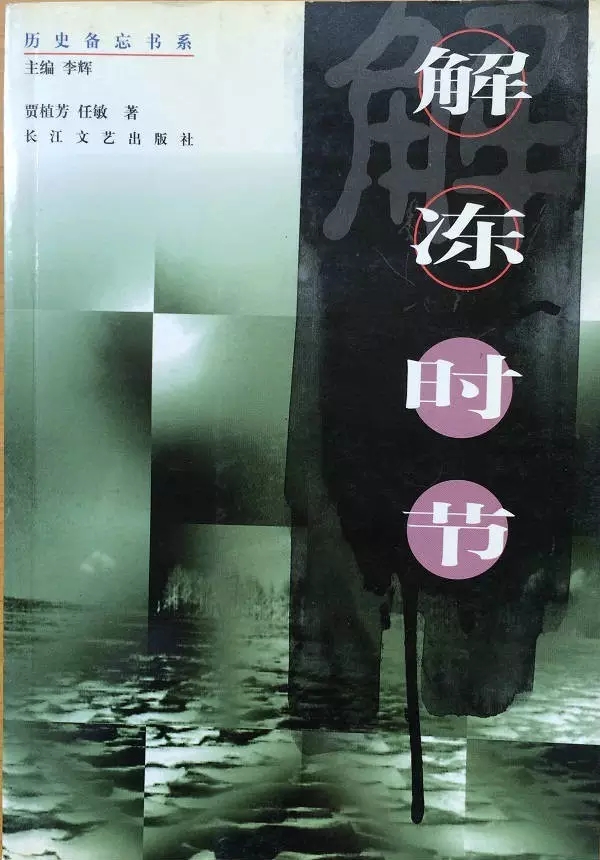
知道了先生和师母的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师母,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他用各种方式各种语言为他们彼此鼓劲。“附信寄来的窗花——一对小鱼,我很感兴趣,联想到我国古代的大作家庄生的话:’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们各自勉励,努力学习改造,争取早日团聚。”(1973.2)
健康,团聚,这便是一对受难夫妻当时最起码、也是最大的愿望。
这些日子没什么事,我身体精神都很健康。处理的事,也许需要上面批示,我这么想,所以还得等等,不能着急。来信说,你常想到这半年来忙于你的生活,想到我穿衣问题,等等。快不要这么想了,我常说,我们现在的唯一要务,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保持两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根本的根本,是最大的财富和幸福,穿的衣服只要能贴体和御寒就行了。你先不必为我的衣着操心,我倒是担心你腿不好,怕受寒,所以很想先把你的棉裤寄回,来信说,预请做一条,那也行,如无条件,即来信,好把旧的寄回。总之,首先要照顾吃饭,我住在大城市里,吃的总比你在乡间强些,每念及此,心里也很难受。但想到这些年艰辛的生活,对我们的改造和锻炼的意义,那收获就很大,也许这就是我们将来能再为人民和革命做些有益的事的最坚实的基础,如我所说,是千金难买的。这么一想,我觉得心胸很是开朗和广大。我想,你也应当有此体会。(1972年12月10日)
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及汇来的8元钱收到了。知道你身体大健,使我精神上的负担得到解除,很甚高兴。虽然如此,但你年纪大了,加上生活的艰苦,应该从这次病中得出教训,重视生活上的保健工作,这样身体健壮,才能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在生活和劳动中得到锻炼,为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建立稳固的根基。要注意劳逸的适当安排;要加强学习,在思想上跟上时代前进。学习剪窗花很好,这也是一种精神修养,使精神上有所安排,集中,这样也能排除一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保持一种内心的安乐和愉快。(1973年6月24日)
你身体都好,我很高兴,反正我们这么拖了近二十年,两个人身体都好,并从艰苦生活中获得很大的思想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还是那句老话,把我们的财力尽量用于支持生活,保持健康,你不能光吃窝窝,要吃细粮,年纪大了,乡下副食品又少,哪怕暂时不要买什么用品,一定要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生活上,精神健康,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1973年7月2日)
你这些日子生活如何,是否吃白面?要吃白面。生活上绝不能过于克苦,以致影响健康。油少,就多吃些蛋,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营养水平,把身体搞好!(1976年11月5日)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这些文字,我明白了。
------------------------------5---------------------------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结束。
读1977、1978年先生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他内心的变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青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1977年10月4日)
今年春节,我去上海看望先生和师母,翻阅他在1978年之后那几年的日记,这些日记,正好与这批家书在时间上相衔接。它们真实记录着解冻时节中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迎来新生,继续走向未来的行程。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成为他的日记中的一个人物。
翻阅它们时,师母在旁人的搀扶下走到先生和我面前。她已重病多年,几次被宣布病危。可是她却顽强地与命运较量,屡次转危为安,被医生视为奇迹。尽管有时她处在昏迷状态,但我相信她未尝一时忘怀先生。她非常明白她的存在对先生所具有的意义。她是先生精神的支柱。她仍然为他而努力活着。
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生命,以动人的情感,为这些家书做着最好的印证。